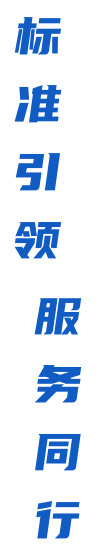出海的最难一关:成为标准制定者

当前,国家、行业之间贸易竞争的核心已由产品转向了标准。视觉中国/图
2025年2月27日,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发布了由中国牵头制定的养老机器人国际标准。
牵头制定国际标准是不容易的。“看不见的短板”——学者林雪萍这样形容中国在构建全球化标准认证能力上的困境。
中国进入几大国际组织的时间,或许能更直观地呈现,短板背后深层的历史原因。
国际电工委员会(IEC)是世界上最早的国际标准化机构,1906年成立。1957年,中国加入IEC,直到2011年、该组织成立100年后,中国才成为常任理事国。成立于1947年的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中国1978年才真正加入,2008年,成为常任理事国。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国际标准的制定上,中国是沉默的。据ISO的数据显示,2000年前,中国制定的国际标准数量仅为13项。这个数据在中国加入WTO后,迎来了增长。从2001年至2015年,中国制定的国际标准达到182项;2015年到2020年,中国主持的国际标准数量超过了800项,但是,之于全球标准总数,占比还不到2%。
对国际标准的参与,近年来,越来越得到政府的重视。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纲要指出,要履行国际标准组织成员国责任义务,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2024年,《贯彻实施行动计划(2024-2025年)》发布,明确提出“实施标准国际化跃升工程”,包括深度参与国际标准组织治理、积极推动国际标准研制等。
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很多代表委员的提案建议都与国际标准制定相关。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宝国建议,加快制定中国白酒国际标准;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提出,要支持龙头企业牵头制定行业标准,助推形成国际标准。
国际标准的制定为何如此重要?有专家指出,当前,国家、行业之间贸易竞争的核心已由产品转向了标准,形成以标准为手段,占领市场的竞争模式。我们试图通过中国的企业、专家在过去十几年里一步步参与主导国际标准的经历,具体地呈现这样一个看似宏大行动的背后,更真实、可感的挑战与意义。
漫长而曲折
“参与国际标准的开始,其实是被动的。”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国际标准化研究中心主任温利峰从事国际标准化工作近20年,她告诉南方周末,深圳特殊的位置决定了这里向外的产业较多,大量的出口贸易企业需要了解国际上对出口产品的标准技术要求。这就倒逼她所在的单位要关注国外、国际标准。不过最初,更多的工作还是集中在“找资料,解读标准,做指标分析”。
她回忆,真正开始推动标准走出去,是在2007年。深圳的光伏企业主动找来,希望在政府的协助下,主导一些光伏建筑一体化的国际标准。当时中国的光伏技术跟国外基本持平,实现了技术的突破。
但这第一次走出去,就让温利峰切实体会到主导一项国际标准的曲折。
按照国际标准的制定修订流程,一个标准,首先要经过对应的技术委员会的讨论,确定是否列入工作计划。然后是投票立项,再进入具体的标准提案过程,同时成立工作组,编写草案。之后,草案将被分发至各个成员国家征求意见,不断讨论、修改,这个过程的反复次数无法预估。在最终出版前,还要经过所有国家的投票。这其中的每个环节,都伴随着相应主体的投票,也意味着,随时有可能被打回、重新开始。
温利峰说,光伏建筑一体化,从立项到最终标准发布,走了近十年。2009年,他们提出项目,委员会开始讨论,2009年立项。之后,她反复邀请国际专家到深圳参加讨论会。直到2012年,才有了阶段性收获,在ISO建筑用玻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下,成立了光伏建筑一体化的工作组,并完成了该项国际标准的立项工作。2018年,这项国际标准才正式发布。
为什么如此缓慢?她解释,建筑用玻璃是非常传统的产业,而在ISO建筑用玻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里的大部分专家,几十年都专注于建筑用玻璃的研究,突然要让玻璃跟光伏结合,对他们而言,是全新的领域,接受新事物需要一定时间。同时,也要邀请光伏领域其他国家的标准化专家加入讨论。
温利峰觉得,在产业层面,参与主导国际标准,技术沟通是最大的挑战,进展缓慢是常态。
相比于技术的障碍,国家间的市场环境和发展差异也让中国企业在推动标准走出去的过程中,挑战不断。
王滨后是海尔集团标准专利总监,他提到海尔主导的第一项国际标准,是2002年提出的防电墙热水器的国际标准提案,这也是中国家电领域第一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标准提案。
那几年,“热水器漏电伤人”事故层出不穷。事后的产品检测却显示,大部分热水器没有质量问题。海尔热水器研发团队在调研中发现,农村和一些老旧住宅存在无地线和接地不可靠的情况。但是,当时国内热水器普遍采用的,是由发达国家制定的国际安全标准,这一标准默认用户家中地线接地良好。
“IEC的大多数专家来自欧美,他们从发达国家的电网状况出发,认为建筑标准非常规范,家里都有接地的,这个标准没问题,不需要改。但他们不知道,当时,不只中国,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住宅没有接地。这些国家参与度低,他们的声音发不出来,现实的问题也就不被看见。”王滨后告诉南方周末,经过大量的现实数据证明和反复讨论,与会专家最终达成一致,这一标准加上防电墙要求,但各个国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用。这个提案,时隔六年,2008年才被正式写入IEC国际标准。这是中国家电企业在IEC标准中“零的突破”。
制定一份国际标准的漫长周期不仅仅体现在与全球各国专家的反复沟通磨合上,对于发起者来说,这其中每一个指标的确立都建立在极其繁重、严谨却又要求创新的工作之上。徐芳是标准化管理及标准制修订的专家,2012年开始专职研究国际标准,她也是海尔智家国际标准主管。
她解释,一个技术指标想要写入国际标准,最重要的是判定指标及测试方法本身是不是稳定可靠。这往往需要通过大量的实验验证,不光是在自己的实验室,要在不同国家的实验室,进行循环比对试验,综合大量数据进行分析。“不同实验室,采购环境不一样,或者文化背景不一样,人们对标准的理解就会不同,所以需要不断调整、修正,才能让一个标准成为可靠的国际标准。”
标准的力量
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参与如此漫长的国际标准制定工作?
《中国标准化》杂志2013年的一篇文章,从数据变化上,更具象地体现了国际标准的力量。
文章提到,弹性结构电压力锅和豆浆机是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基于这两种产品所提出的电压力锅和豆浆机系列提案于2012年写入相应的国际标准。当时,美的集团提供的数据显示,制定国际标准前的2009年,美的出口额仅为不到20万美元,2012年增长至近400万美元;九阳公司2009年豆浆机产品出口量为6万台,出口额232万美元,而2012年的出口量提高到15万台,出口额接近1000万美元。
徐芳对南方周末说,一个新产品要打开全球市场,解决标准问题的重要性在于,所有市场最终用同样的标准、同样的测试方法来判定产品是否合格,“不能这个国家的实验室这样判定,另一个国家的实验室那样判定,这个市场合格,那个市场不合格,这会为产品全球上市带来很多困扰。”
有时,提出一项国际标准,也有更具战略意义的考虑。徐芳说,2014年,海尔在IEC日本东京年会上首次提出了冰箱保鲜标准提案,2015年IEC明斯克年会上,推动成立了IEC TC/SC59M WG4冰箱保鲜标准工作组。在冰箱百年的发展史上,技术变革一直建立在制冷和能效上,当时,已经卷到天花板了。对于企业来说,想要突破,一定要从用户需求出发另寻出路,“要把创新技术,从标准化的角度,塑造为市场竞争力,更大范围地引领行业技术风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吴国鼎进一步解释了标准带来的直接竞争力。“当一个企业有了技术专利,又将这种技术主导为国际标准后,别人要用,首先要经过你的授权。授权虽然不会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社交手段,有助于企业的全球布局。此外,标准背后还有技术的专利,你要收专利费,这是最直接的效益。”
即便不主导一项国际标准,积极参与其中,也会得到实际的反馈。
温利峰回忆,2015年之后,她从推动产业的国际标准转向组织治理的国际标准。在组织标准制定过程中,一些与我国国情不适用的条款得以修改,温利峰说,其中有一些条款常常要按地域划分治理的高中低风险。在讨论过程中,她几次力争删除,“这个准则怎么确定?万一被定为高风险地区,就是不受信任的。我们认为,这样会阻碍那个地区产业的发展,而且它本身就是不公平的。”
积极参与意味着,一旦发现有不适合中国的,或对中国产业有歧视的条款,可以提出修改意见。否则,这就会成为中国企业的阻碍,导致无法通过第三方认证。“如果你拿不出第三方认证,就要从其他方面证明自己有,可能包含80条问题的解释、填N多资料,无形中就增加了企业出口的成本。”
温利峰说,也是因为积极参与ISO反贿赂管理体系标准的编写,国际标准化组织机构治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得以成立。她也成为这个委员会在中国的技术对口单位负责人。目前,技术委员会编写了20个左右的国际标准,中国主导的占了40%,在整个技术委员会的各工作组领导职务中,中国专家占了60%。
难在具体的人
在过去十几年里,中国在国际标准的参与上,有了很大的突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委)发布的《中国标准化发展年度报告(2023年)》显示,国际标准制定参与度达到82.2%。
南安市中机标准化研究院院长朱斌在一篇论文中指出,从参与度来说,中国在世界上的确名列前茅,甚至超过了美、英、法、德、日等国家。但是,主导制定的国际标准总体数量相比发达国家,影响力有限。
吴国鼎告诉南方周末,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但现有国际标准中90%以上都是西方国家提出和主导的。中国主导制定的国际标准占比仅为2%左右。
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于成本。朱斌指出,国际标准制修订的成本,通常只有政府标准化机构和大中企业能承担得起。根据《国家标准制修订经费管理办法》,标准经费的开支项目,包括资料费、设备费、试验验证费、差旅费、会议费、劳务费、专家咨询费等十项费用。相比国家标准的制修订,一项国际标准从立项到发布,短则两年,长则四五年,各项费用开支较高。他认为,对于主导和参与国际标准制修订的企业,应该加大资金扶持,提高参与的积极性。
温利峰表示,她所在的深圳标准技术研究院,每年拨款几百万元支持他们开展国际标准工作。但这并不是每一个地方都能负担得起的开支。
经济学家贾康对南方周末分析,中国在国际标准制定中,存在一些隐性的不足,包括对国际规则的理解、文化差异的适应、全球产业链的整合能力等。“这些短板往往不易察觉,却可能对标准制定的成败有决定性影响”。
贾康认为,更薄弱的地方在于,在一些传统和高精尖领域,中国仍缺乏核心技术,导致标准制定话语权不足;有些企业和机构对国际标准制定的规则和流程不熟悉,也会使得提议被否决或边缘化。同时,政府、企业和研究机构之间协同不足,不易形成合力。
温利峰发现,中国更广泛地参与国际标准,是近几年才变得积极的。她从2006年开始出去参会,直到2015年,很多参会的国内专家还是比较游离的状态,并不积极讨论。
国际标准的制定建立在国家实力和技术突破的基础上,但真正执行这些工作的还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温利峰认为,目前中国在国际标准化方面,最大的匮乏也在于此。“语言是第一关,你还要理解标准化,对技术也要非常熟悉。”此外,还有更多的技巧和应变能力需要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不断学习领悟,“这是没办法教的”。
“比如,是不是能以非常平等、开放的态度去跟所有人交往?”温利峰发现,有时中国的一些专家觉得老外不理我,那我也不理对方。“这是不行的,该做的事情就要推进。他不理,你可以适时地提醒,他也许就是忙,你得让他知道,你是认真对待事情的,久而久之,他会觉得你是可信任的。”
积极参与并不是一句口号。温利峰说,它体现在非常细致的工作中,“即便是其他国家的提案,你是不是能够主动加入讨论、投票;即便你反对,如果最终方案通过,进入编写环节,你是不是也能加入进去,全力以赴地写;甚至在反对之后,提出一个可以帮助解决的方案。”
徐芳称自己是“技术的翻译官”,但很多时候,她的工作也不仅关乎技术。
2015年,海尔要推出卡萨帝双筒洗衣机,随之开始了国际标准的制定。徐芳说,当时国外很多专家不理解,这不就是两个机器叠加吗?为什么不直接买两台机器?“他们一般不太受家庭空间的影响,有专门的洗衣房,一台洗衣机、一台干衣机是标配。”文化差异,也让这些专家无法理解中国消费者的痛点,“中国家庭会特别注重小朋友的安全,希望把孩子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但对于欧美人来说,他们并不Care。”大会上,她的这个理由并没有说服与会专家。
会期短短几天,日程安排也很满,每个人的发言可能只有10分钟、20分钟,徐芳就利用吃早饭或者休息的时间,找委员会的各个外国专家聊。“不在乎宝宝和大人的衣服是否分开洗,那深色衣服和浅色衣服呢?面料好一点的毛衣和牛仔裤呢?是不是需要两个不同的程序?”
很多时候,得到理解和支持就发生在这样的场合,而不是那十分钟的发言。最终,这一标准获得通过,也为这个创新产品打开了通向国际市场的大门。
成为战略目标
近年来,在政府文件中,也可以看到标准的国际化被抬到了日益重要的位置。
2021年《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发布。《贯彻实施行动计划(2024-2025年)》又明确提出“实施标准国际化跃升工程”。
北京、上海也在2022年相继发布了围绕标准化发展的文件。《首都标准化发展纲要2035》提出,到2025年,北京要制定国际标准80项以上,争取若干国际标准化技术机构秘书处在京落地。《上海市标准化发展行动计划》明确,到2025年要牵头制定修订新的国际标准60项、新增国际标准化组织注册专家200名,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标准化高地。
梳理相关政策会发现,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每年都会发布《全国标准化工作要点》。近几年,逐渐加强了对国际标准工作的提及。以往,围绕国际标准相关的内容,都是在文件靠后的位置,大多分布在第四、五、六条。2024年,它被显著地列在了第二条。
刚刚结束的2025年全国两会,诸多代表委员也在关注各自行业参与国际标准的问题。
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宝国认为,茅台、五粮液等头部酒企市值位居全球酒类企业前列,具备参与国际竞争的实力。但中国白酒企业“走出去”仍面临国际标准缺失等挑战。应该加快制定中国白酒国际标准,与主要烈性酒生产国加强沟通,积极参与国际标准谈判,构建适应国际贸易的白酒标准体系,提升中国白酒在国际烈性酒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
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提到,由于早期光伏市场主要在海外,应用IEC/ISO国际标准,接受海外认证机构的测试,中国企业参与标准和认证工作不多。目前中国光伏产业技术水平已经全面领先,但所采用的标准不仅跟不上行业发展的需要,还受制于发达国家,限制了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为此他建议,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织制定行业标准,助推形成国际标准。
不仅是中国。据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网站2月19日消息,韩国国家技术标准院将对提高国家标准技术能力的事业投资425亿韩元(约合2.15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加了22%。其中117亿韩元将重点投向需要率先实现国际标准化的12个尖端产业领域。
学者林雪萍在《大出海》一书中总结,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品牌,再到中国认证,是中国制造全球化向上攀登要面临的越来越陡峭的天梯。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原主席张晓刚曾撰文指出,发达国家非常重视新兴产业标准。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至今,世界各国纷纷提出了制造业振兴计划。这其中,重点就包括发展先进制造业和注重产业发展中的标准引领。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曾表示,“用工业4.0标准为人类文明与进步作出德国贡献,用工业4.0标准引领制造业升级,确立世界制造业领导地位。”
张晓刚认为,对于中国来说,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点就是解决制造业大而不强的问题,而标准化就是高质量发展的抓手。

图片由农健使用AI工具生成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梁婷
责编 张玥